
Business School
商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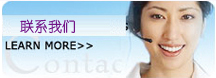
手机:13521943680
电话:010-62904558
工商管理博士: 论学术界能力需要改变心态
去年,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的博士毕业生中,残疾的早期职业研究人员人数不足。
在美国,25% 的成年人有残疾,但到 2020 年,听力或视力受损的人仅获得美国 STEM 博士学位的 4%,而行动不便的人仅获得 STEM 博士学位的 1%。
英国皇家学会 2021 年 1 月的一份报告发现,在 2018-19 学年,12.5% 的英国 STEM 毕业生有残疾,高于 2007-08 学年的 6.1%。这种上升归因于报告心理健康状况和学习困难的学生人数增加。2019 年,身体残疾者约占英国 STEM 研究生的 2%。
在纪念美国全国残疾就业意识月(10 月;类似的英国活动,残疾历史月,从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18 日)的第二个专题中,四位残疾早期职业研究人员讲述了他们自己在应对残疾问题上的经历。学术界以及他们如何克服研究领域的障碍。较早的一篇文章重点关注残疾群体领袖,以及学术界的残疾文化——贬低和歧视残疾人的信念或做法(无论是身体状况、心理健康问题、慢性疾病还是认知差异)——需要改变(见Nature 598 , 221–223; 2021 )。这些初级研究人员描述了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如何更好地倡导实验室团队的可访问性和包容性。
SARA RIVERA:不要做假设
密歇根大学和安娜堡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微生物生态学家和博士后研究员。
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本科第二年时遭到性侵犯后,我接受了焦虑、抑郁和惊恐发作的治疗。我失去了我的短期记忆。大学的性侵犯预防和意识中心写信给我的教授,解释了情况并列出了帮助我的步骤,包括推迟我的考试。
袭击发生八个月后,我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并获得了一些课程延期。我晚毕业了一个学期,并于 2014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开始了研究生学习,比我预期的晚了一年。我认为到一个新地方会有所帮助,但我离开了我的整个支持网络和我的家人回到了密歇根州。
进入研究生院三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危机咨询中。研究生院在很多方面都在重新遭受创伤。我在与我的顾问开会时惊恐发作,我被重新诊断为 PTSD。
我求助于我在密歇根州建立的支持网络。一位前教授建议申请一名博士后,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某人共同建议,以探索联邦研究选择。我成功了,并于 2020 年再次开始在密歇根州工作。
担任新职务后,我询问了报告残疾的流程。我告诉我的两个博士后顾问,“我有这种残疾,我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是我需要的一些便利条件。” 这是开始新工作的尴尬方式——但现在我每周工作四天十小时,而且我远程工作。我依靠保持时间表来控制我的心理健康。在本地拥有我的支持网络和我的家人真的很不一样。我是西班牙裔,家庭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重要。
我现在的顾问非常支持人们抽出时间处理自己的健康问题。我因为没有安排假期而被召唤。缺勤叶应归一化。我给别人的建议是:你不知道其他人发生了什么。不要假设某人很懒惰或不在乎。请记住,当有人在心理健康问题上挣扎时,他们很难评估自己的心理状态。不要把人当废话。
VANESSA CRISTINA DA SILVA FERREIRA:为所有人创造公平
巴西塞罗佩迪卡里约热内卢联邦农村大学聋人科学和数学教育硕士生。
2014年,大学本科第二学期的第一天,我被车撞到脚踝严重受伤。我不得不坐轮椅六个月,我妈妈不得不和我一起去上课。接下来的学期非常艰难:我再次学习走路,我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
我花了六年时间才拿到物理学本科学位。由于难以驾驭庞大的校园,我每学期上的课都较少。我有很棒的支持我的朋友,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有他们的态度。
有一集中,我在二楼上了一堂实验课,但电梯从来没有工作过。我不得不请朋友帮我上楼梯,然后他们会回去拿我的轮椅和我的包——这是一个巨大的手术。对于我们的期末考试实验,我们不得不分成两组,因为没有足够的设备。将有一个抽奖,看看哪个班级第二天必须回来。一位朋友问教练那天我是否可以去,因为我已经爬上了楼梯,但另一位学生说把我从抽奖中抽中是不公平的。
我的教授们都非常支持,但当时我所在的大学没有处理残疾问题的办公室。我问教授和管理人员我是否可以在校园的建筑物之间乘车,但他们说不可以。相反,他们建议我可以通过给教授发电子邮件和安排考试来在家学习。(这是在大流行之前,所以没有远程讲座。)但我想上课。那是我的权利。
我在葡萄牙度过了一年,学习葡萄牙手语,并为聋盲学生教授科学。我在那里的经历非常不同。电梯一直在工作。我问大学是否需要我的残疾证明,管理人员和我的主管说,“不需要,如果你说你有,我们相信你。”
我用一根拐杖来稳定,因为我的右腿比左腿弱,而且我的脚踝很容易滚动并让我摔倒。我很痛苦,不能走路或坐太久。我有时需要在课堂上休息和伸展。
现在,校园里有一个工作组来解决残疾学生的问题,但他们并不总是听到我们的声音。当我表示担心被限制在远程课堂上时,一位高级研究员驳回了我的担忧,声称她 20 年的包容性研究经验并不支持我的担忧。我是每天都生活在行动不便和多动症中的人。我今天不能把它们放在盒子里,因为我不想去想它们。他们是我的一部分。
在大学校园里,学生和教职员工只需要询问人们是否需要帮助。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如果残疾人说“不,谢谢”,那么他们必须接受这一点,而不是被冒犯。有时,我们需要一个人去或尝试为自己做点什么。
我本科毕业后,一些残疾学生和教职员工组成了一个支持和倡导小组。总之,我们更有能力要求大学提供更好的可及性和政策变化。2021 年 7 月,我们让大学在其申请硕士学位的政策中添加了无障碍权利。
当我在使用轮椅时遇到所有这些问题时,我得到了大学清洁工的大力支持。他们问我是否需要什么,总是微笑着鼓励我。在我的荣誉论文演讲中,我感谢这些女性,因为她们对我的成功非常重要。他们是其他人有时看不到的人——就像残疾人一样。
有些人认为残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特权,但实际上残疾学生需要公平——而不是平等。有了平等,我们将一事无成。但在公平的情况下,所有学生都可以使用相同的设施和教育。我们不能放弃,即使有时很难。我不会安静的。残疾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残疾只是人类的另一个特征。
Logan Gin 站在白板上的踏脚凳上向同事解释研究概念。
Logan Gin 向本科生解释了一个研究概念。
LOGAN GIN:残疾不是一个肮脏的词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生物教育博士生,研究残疾学生的本科 STEM 体验。
我患有灾难性发育不良,一种侏儒症,这意味着我使用前臂拐杖四处走动,并使用电动滑板车长途跋涉。长时间站立和接触事物可能具有挑战性。我经常浏览不是为残疾人士建造或设计的空间。
尽管我在这个领域面临无障碍问题,但我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主题一直在 STEM 挑战我自己。
作为一名本科生,我不得不在我大学古老的丘陵校园中穿行。坡道被钉在建筑物的背面。我会通过后台入口进入一个演讲厅。大学在传递什么信息?
对于希望成为 STEM 社区一部分的残疾学生,我努力应对这些挑战。对于生物和化学实验室课程,所有的长凳和通风柜都是为中等身高的人设计的。课程讲师会尝试设置一个平台或凳子,我可以站在上面拿东西。但它最终成为一个安全问题,因为我不习惯从这些表面接触化学物质。
解决方案来自我的实验室伙伴,我很早就认识的另一个学生。我们组成了一个很棒的团队:他负责所有的实际操作,而我负责数据收集和分析。我们按照日程安排一起参加所有实验室课程。他明白我需要什么,我能够做出贡献。
当我讲这个故事时,我说我感到非常幸运。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参加第一年的实验室课程,并且有一个不适合他们的合作伙伴,或者一个不适应的实验室协调员,然后他们就完成了 STEM。就是这样。
在很多方面,我对从事科学研究的物理方面感到厌烦。我不得不考虑是否要继续应对在物理空间中导航的压力。我没有,所以我找到了一个替代领域:教育研究。现在,我 99% 的工作都在计算机上进行。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我的身心健康。现在,我的目标是让那些跟随我的人更容易浏览这些空间。
科学中有许多领域,尤其是计算科学,不需要体力消耗。但学生不应该因为他们有残疾而被引导到那些人身上。我们能否为所有学生创造真正可访问的体验,以选择他们想要的任何领域?
在研究生院,我和我的博士导师都发现很难在我们实验室组的空间中获得我需要的住宿条件——即使是简单的东西,比如一个可以够到水槽的凳子。作为一名在残疾办公室注册的研究生,我被告知,“我们只处理与课程作业相关的住宿。这是一个人力资源 (HR) 问题,因为您是一名员工。” 然后,因为我是一名学生,HR 会让我回到这个残疾办公室。
最后,我的住宿费用由我的顾问和我的部门分担,因为他们希望我成功。我需要的是便宜的,但其他自适应设备可能很贵。如果首席调查员认为这超出了他们的预算,他们是否会想要招募和留住残疾研究生?
与教授、导师和残疾办公室进行自我宣传的负担往往落在学生身上——这需要时间、精力和精力。试着找出那些对你有兴趣的人。寻找那些想为你打球并在学术界挑战能力主义的人。有时人们无法提供帮助,但会将您与可以提供帮助的人联系起来。
检查无障碍需求应该是实验室组的规范,而不是特殊情况。社会终于到了“残疾”不是一个肮脏的词的地步,但我们需要经常讨论可访问性。
DIVYA PERSAUD:问问我们需要什么
伦敦大学学院空间和气候物理学博士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远程工作。
我在本科课程进行到一半时患上了致残性慢性病,在此期间我请了三段病假。在我的空间和气候物理学博士课程之前,我还休假了一年。
学术界在容纳残疾人方面存在很大问题。尽管我在我的大学注册了我的残疾作为本科生,我仍然难以获得录制的讲座,并且我的成绩因不上课而被扣分。我通过阅读教科书自学,并尽可能地进来。
我处理了很多敌意。一些教授告诉我,我需要更好地沟通,但我不想对我的病情直言不讳。然而,除非我把它全部放在桌子上,否则我没有得到我需要的帮助。我有时会建议人们要令人毛骨悚然:尽管您有隐私权,但如果您不完全披露您的残疾情况,则被解雇是很常见的。
我的一位非正式导师向我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住宿。她告诉我在任何舒适的地方工作。她还把我当作一名研究人员,让我把自己看作一个人。我选择了我知道会接纳我并尊重我的自主权的导师。如果您是 STEM 领域的有色人种女性,就像我一样,非正式导师可以帮助您保持理智。
我的情况不断变化且不可预测。我经常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取消承诺。在外面,我看起来很脆弱。非常谦虚:我必须优先关注自己的身体,并说我不能亲自参加某些活动。
但我也了解到人们不应该经常道歉。这告诉其他人(和你)这是你的错。不停地道歉会影响你对自己的看法。相反,我会说,“谢谢你的耐心”,或者“我不能在下周 100% 承诺”。另外,要自信一点。仅在有助于获得某些信息时才披露私人详细信息。
如果您想为残疾同伴代言,只需询问他们需要什么。这会很尴尬,但这就是生活。不要停止要求您的残疾朋友出去。未经同意,不要出于善意而做事。永远不要向其他人透露某人的残疾。
并且不要假设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是健全的。要打破残障思维,参与残疾人的工作:观看残疾科学家的 TED 演讲并阅读他们的话。我的首选活动家是 Alice Wong,他编辑了 2020 年的Disability Visibility一书,以及 Lydia XZ Brown,他撰写了关于神经多样性的文章。
试着重新审视你对有不同需求的人的看法。走进实验室或教室并考虑:这个空间使某人致残怎么办?椅子?缺少坡道?谁不能去远足?这个事件是在伦敦的老建筑中呈现的,不包括人吗?
我想了很多:因为残疾,我们在我们的领域缺少谁?

